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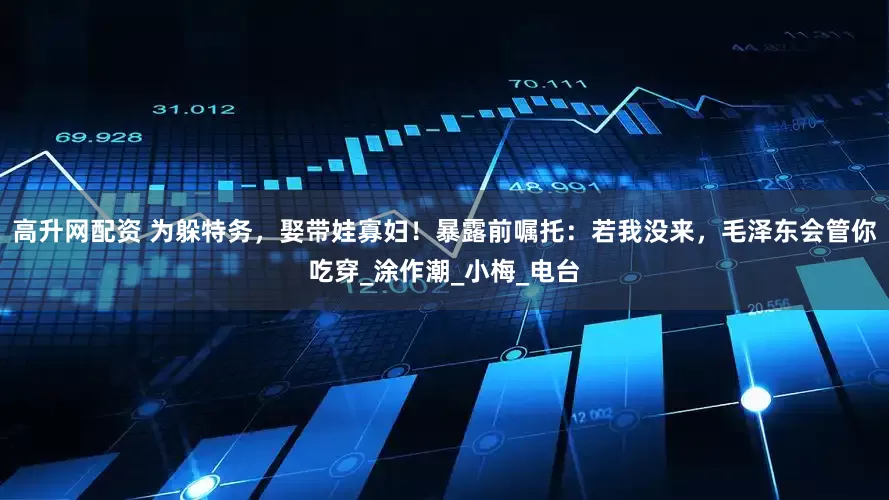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他娶的不是爱情,而是一张伪装身份的“船票”,多年后,他失踪前留下一句话,让人心头一紧。
木匠开店的背后,全是局展开剩余93%1930年,上海法租界乍浦路口,一家“恒利无线电修理店”悄悄开张。
铺面不大,招牌也不显眼,街坊看久了,只当这家店主是个会修收音机的木匠,没有人知道,这家铺子背后,藏着中央特科的秘密电台。
那年冬天,涂作潮从香港绕道进了上海,头发理得很短,手上有老茧,穿的是布衣长衫,看不出一点“特务”的影子。
他用假名蒋林根注册店铺,房租是潘汉年,提前托人打点好的。
邻居们只知道,这人手艺不错,修得快,说话少,不抬头,实际任务,是主持特科在沪的无线电工作。
中共中央情报系统从南昌、武汉转移后,急需建立独立、安全、可控的通讯体系。
他白天接活修机,晚上调频发报,手边那台半导体机箱,外壳看着粗糙,里面线路接的是延安的心脉。
涂作潮技术出身,早年读过几本物理书,在广州时期便参与电台建设。
动手能力极强,能把碎铜丝做成简易天线,能把坏掉的电容修得比新买的还稳。
“恒利”店里不少零件,其实是专人从香港运来,再由地下党员送进来的。
秘密电台每天凌晨两点开机,只收不发,收到的情报,他抄写一份,用化名投进法国公寓楼下的报箱,专人清晨取走。
一来二去,电台成了“心脏”,他成了没人知道却扛着全局的“隐身人”。
外面风声越来越紧,租界巡捕房几次来查铺,装的理由是“无照经营”。
有一次来了个探员进屋就敲桌子,边敲边说:“修收音机的这么多,你生意这么好?”
涂作潮没回话,手里一边拧螺丝,一边慢慢把机壳盖上,对方拿不出凭证,只得撂下一句“再来看看”,甩门走了。
潘汉年听后脸色沉下来,说:“你这身份要出事,整个系统都要瘫”,涂作潮点头,不多言。
第三天,就关了“恒利”,又换了地方,名换成了“宏昌修理铺”。
敌人盯得越来越紧,身份再隐蔽,也不能单靠“店铺”。
潘汉年当面说:你得成个‘老实男人’,得有‘家’才不惹眼。
娶个带孩子的寡妇,不是为了成亲找“老婆”不是为了过日子,而是为了活命。
张小梅是个纱厂女工,读不成书,进厂早,丈夫死得早,带着个五岁大的孩子,投奔姐姐。
租在租界边上一处小楼,抬头能看见电线杆子歪着,楼下是菜摊和炭铺,为人老实,没背景,没亲戚来往,正合要求。
中间人是工厂里的医生,受过联络员嘱托,只跟张小梅说:这人正经,开店做手艺,老实。
张小梅没多想,主要孩子要上学,她也想有个能一起撑家的男人。
婚礼简单,没有酒席,没有亲戚,租界里登了纸,邻里都知道“张寡妇改嫁给修电台的木匠”,外人看去,这桩婚姻合理得不能再合理。
婚后,张小梅继续进厂,涂作潮在家修理,孩子改姓蒋。
邻居说:“这男人是哑巴,好像不爱说话”,张小梅笑笑,说:“他就爱鼓捣那几根线。”没人怀疑。
屋里头,电线穿墙走天花板,一张大桌子钉着三层隔板,全是接线盒、收发器,还有一台纸包的密码机。
张小梅不敢碰,她也不懂。
涂作潮跟她讲过一句:“这些是国家用的,不许动。”她记住了。
几年里,涂作潮换了三个铺子,张小梅换了两份工作。
他从不在晚上九点后出门,也从不带陌生人进家。
一次,楼下住户招待远亲来吃饭,有人想借水龙头洗手,他出来挡住,说水管坏了,那人一脸疑惑,回头小声说:“那家男人怪得很。”
实际上,墙后藏着密台,那水管口正连着电源通道。
一次接报失误,让他被上级责备,说:“这台若落敌手,全上海会死人。”他没辩解,只点头收拾东西,三天内搬家换频率。
张小梅不知道真相,也没问过。她只知道丈夫常说:“你和孩子要吃饭,要活下去。”
有时候她说“你出去也小心点”,他总嗯一声,不多说。
外头,巡捕和便衣特务越来越频繁,有同行无线台被捣毁,人被抓走,三天后人没了消息。
涂作潮知道,自己暴露是迟早的事,他开始准备后路,悄悄把所有金条封在瓦缸底下。
1942年中秋那晚,涂作潮从外面回来,脸色很沉,饭没吃几口,说得最多的一句是:“如果我哪天没回来,你就带孩子找延安,找毛主席。”
张小梅听了,眼圈红了,她不知道这句话有多重。
身份暴露前的最后一夜1942年秋,上海一场雨下了整整三天,弄堂潮湿发霉,墙角的砖缝都透着水汽。
屋里那台电台,像往常一样,在凌晨一点零三分通电,涂作潮没说话,只拿毛巾裹住手,扣住耳机,一边听一边记。
前两天,潘汉年转来的口信,已经说得很明白——有人在法租界秘密递交了一份名单,其中提到一个名字,叫“蒋林根”。
这个名字在他耳朵里一炸,就跟枪响一样。
纸上没写真名,只写“蒋”,但细节对得太准。住址模糊,职业写着“修理收音机”,备注一行字:“长期晚间活动,疑似地下电台操作员。”
情报从敌特高组传出来,线人名字写着“密代013号”,他没问是谁,也不打算追查,只知道时间不多了。
他把密码表翻到最底页,把编号抹掉,把信号频率调整成变动模式,然后把电台每条输出线都过了一遍电压。
这一夜,不接电报,不发信号,只留个“盲监听”,他想看最后有没有信任的人传来只字片语。
张小梅早就感觉到不对,前两天开始,男人每天吃饭时都用左手擦筷子,眼神不看人,连孩子喊“爸爸”都没回头。
那晚,饭刚吃完,涂作潮把柜子打开,从最下面拉出一个布包,里面包着几块黄灿灿的金属条,还有一封信。
没解释什么,只把信和金条包好,再次用布封死。
信藏进墙角砌缝,金条封进水缸底部,用厚布和砖压着。
屋里没声,只听见孩子在另一头咕哝。张小梅拿布擦桌子,没吭声。
第二天一早,天没亮,涂作潮穿了一件棉夹克,裤脚扎进棉袜里,门口一包工具袋,一台电台主机,没说去哪里。
只留一句话:“要是我没回来,你就按我说的做。”
张小梅问:“你去哪?”涂作潮停了几秒,说:“去个地方,看看能不能不死。”
门关上了,鞋踩水的声音渐远。那声音,成了她记忆里最后一次动静。
整整两个月,她没再见过他。
房东问铺子要不要续租,她说:“不开了。”工厂同事来问她男人去哪了,她说:“回老家探亲。”
只留下信和金条,兑现那句话的人来了1943年冬,上海局势更加混乱,大批日军宪兵开始清查租界边缘区域,凡是住户登记不清、来历模糊的,一律排查。
张小梅那晚,坐在小炕上,拿出那封信,看了一晚。
她不识字,看不懂内容,只知道那是他临走前藏下的最重要的东西。
她没动水缸,那水缸就在屋角,里面水已经干了,底部蒙着一层灰布,上头压了半块石板,她想,如果哪天真要走,就带上这点“命”。
屋里灯泡坏了,她没换,孩子说冷,她让孩子套两层袜子,没钱,没胆,也不敢动信。
有一次,邻居家来人,说有人正在查旧厂房的职工,前几天那个姓林的男职工,已经被带走问话。
她一夜没睡,把信转藏到衣柜顶,把水缸底部那块布压实,用油泥封死。
那时候,她才开始想,到底有没有那一天——有人来找她。
一直到1946年春,一张老照片突然被送到了她手上。照片里,涂作潮站在电台前,背景是他们家那间铺子,墙上还贴着旧日历。
带照片的人说:“组织找你很久了”,张小梅没说话,脸埋进围巾里。
那人没等她说,就开始往桌上放东西——布票、粮票、介绍信,还有一张联络地址单子,说:“他留了后手,说你会留下来,也说你会交出信和东西。”
她当晚交出了那封信,交出金条,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写在纸上,递给那人。
过了两天,那人又来了,说组织已经安排孩子上学,让她搬去江湾区,有接应人。
她没问丈夫在哪,只问了一句:“他的事还在做吗?”对方点头。
她就点点头,没再说一句话。
新地方住进去后,她把铺子照片贴进镜框,挂在灶台旁。没人问,也没人提。她每天烧水、做饭、带娃,活得像个普通市民。
一次,原工厂老同事来访,看到那照片,愣了一下:“你家那位……还在吗?”
她只说:“他走得早,走得干净。”
后来,孩子考进技术学校,听人说起父亲往事,才知道自己家里的那些“布票”和“介绍信”,是很多人做梦都求不来的。
那天夜里,他问母亲:“爸爸干什么的?”
她头也没抬,只说一句:“他让我们活下来了。”
之后没人再提起涂作潮,只有她自己知道,那一年冬天,那间铺子关门时,他说过一句话:“你带孩子找毛主席,他会管你吃穿。”
几十年后,那句话还挂在她心里,没凉过。
参考资料: 《涂作潮:为天论曲直 不改绳墨心》·中国军网·2023-12-13 《纪念西电教员涂作潮诞辰120周年 | 本为“木匠”,却做了李白的老师,将“电台”变成“收音机”,救出入狱8个月的战友》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·2023-07-05 《红色木匠涂作潮》·西安党史网· 2022-04-17发布于:河南省通弘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